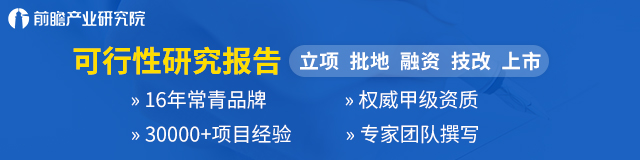口述历史:侵华日军慰安妇的悲惨人生

口述历史:侵华日军慰安妇的悲惨人生
在日军侵华期间,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,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,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。因为种种原因,大部分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受害人都已经相继离开了人世间,许多人至死都没有说出自己的那优悲惨而又羞辱的经历;目前仍然活着的受害人已为数不多,并都是高龄多病,她们要把自己的那段经历告诉所有的人,要把那段历史告诉所有的人。
生于1927年12月,海南陵水县鸟牙峒人。1942年春被日军抓至砧板营军营长期奸污,3个月后被押往崖县藤桥慰安所成为慰安妇,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。
椰林越来越密,路越来越窄。在离开公路后不久,车终于停了下来。通往村里的路变成了一条只能容一人穿行的小道。同行的人告诉我,由于偏僻,几十年来鸟牙峒变化很小,60多年前日本人进村走的也是这条小道,这是进村的唯一一条路。
小道两边密密的椰林间,隐约看见搭建在其间的房屋,人们透过密密的树隙悄悄地打量着进村的人。
鸟牙峒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。1940年9月,日军侵占了鸟牙峒,在鸟牙峒建立据点后,日军即在鸟牙峒军营中设立了“慰安所”,当时仅4000余人口的鸟牙峒,就有20多名少女被强迫抓去充当了“慰安妇”。“慰安妇”中年龄最小的仅十三岁,最大的不超过十九岁。
在村子的中心,我们来到了一排低矮的小屋前,屋前有块不大的平整场地。带我进村的人就站在屋前那块平整的场地上喊:“阿婆啊!”这时从小屋侧面的一间用椰树叶搭成的茅舍里,探出一位老人的头来。我知道这就是陈亚扁阿婆了。
老人把我们领进堂屋,屋里有些暗,潮湿。堂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,床上铺着光洁的席。老人请我坐到床沿上,然后就赶忙转身进了房间里,不一会出来时,她一边用手扣着纽扣,一边用手抹着头发。老人换了一件干净的衣裳。
老人就坐在我对面的一张小矮凳上,同行的人用海南话告诉她我是记者,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她。老人便点头,朝着说话的人,也朝着我,然后就看着我,像在期待着回答我些什么。
而事实上第一次在衬亚扁阿婆家,我什么也没有问她。我和老人面对面的坐着,这时她17岁的孙女来看她。老人拉着孙女儿的手,亲切而又平静地说着话。她们说了些什么,我听不明白,那时我只是一直在猜想老人当年被日本兵抓走时,是不是和她的孙女儿一样的美丽?老人在看着孙女儿时,不知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那段凋零的花季?
第二次去陈亚扁阿婆家,是在一个星期之后。当时她仍请我坐在那张铺着光洁的席的木板床上,她仍到边屋里换上了那件干净的衣裳,然后仍坐在我对面的那张小矮凳上。但这次她没有看着我,而是拿过放在墙边的那个用塑料可乐瓶改造成的水烟筒,她慢慢装好烟丝,然后将烟筒堵在嘴上,点燃。老人深深地吸了一下,又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,说:“孩子,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,你问吧。”
老人再次深深地吸了口烟,然后再慢慢吐出。她并不等我问,便开始了她那辛酸地叙述。
1942年,乌牙峒的春天和往年一样,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到来了。门前屋后的椰树并没有和其它的季节有明显的变化,只是由于一场接一场的雨,让这个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春天都要冷些。
我出生在1927年12月16日的那天清晨,1942年那一年我刚刚15岁。因为出世的时候,浑身红润,脑儿扁平,长得非常可爱,父亲就把我取名为“亚扁”,“亚扁”在黎语中是美丽非凡的意思,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。我的父亲陈其义是甲长,他精明能干,为人正直,办事公道,很受乡亲尊敬;母亲善良贤淑,善于持家。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,我排行老三。虽然家庭谈不上富有,但吃穿应酬一年四季不愁。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
1942年春天的一个中午,当时,我正在家中的堂屋里编织桶裙,和我一起在家干活的还有刚过门的嫂子,和还没出嫁的姐姐,她俩在舂米,我们三个人边干活边说着话。
突然,两个日本兵闯进了家门,我们姑嫂三人被端着枪的日本兵吓得扔下了手中的活,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是好。日本兵叽哩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话,眼睛在我们姑嫂三人的身上一遍一遍来回地扫着,最后停在了我的身上。这时两个日本兵就将被吓呆的姐姐和嫂子赶到屋外,然后拉起惊慌得浑身发抖的我调戏。他们先用匕首割断系在我身上的连着纺车的缠带,接着就拼命地在我身上乱抓乱捏,最后剥光了我的衣裙,把我按倒在地上,轮奸……
我拼命挣扎,疼得撕心裂肺地喊着,可他们不管我死活,边强奸边兴奋地狂叫。我的身体大量出血,直到我昏死过去他们才罢休。
从那以后,那两个日本兵就经常来欺负我。有时把我抓到军营中,有时就在马背上,或者在村寨外糟蹋,稍有不从就会被毒打。
后来,日本兵就干脆把我关在了军营里。和我一同被关进军营的还有同村十七岁的漂亮姑娘陈亚妹,我们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房里,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,不准走出军营一步。我们成了固定的“慰安妇”。
每天晚上我们都要遭日本兵强奸,一个人至少陪两个,多的时候三、五个不等。
在军营里,我还见到其他20多名姊妹被抓进来,白天,她们给日本兵干杂活:洗衣、煮饭、种菜、拾柴……晚上,她们被逼着为日本兵唱歌跳舞,给日本兵挑水洗澡擦身,还要陪他们睡觉,日本兵随意糟蹋她们。我和陈亚妹,日本兵不要我俩干重活,白天我俩给日本兵做饭用的大米挑挑砂子,在院中收拾收拾房子,夜里就被他们糟蹋,有时白天也逃不掉的。
3个月后,砧板营日军奉命把我押送到了一百多里外的崖县藤桥慰安所。
在藤桥慰安所,日本人把我关在一个盒子式的木楼上,楼下还关着其他姊妹。每天晚上,都得忍受日本兵的糟蹋,遇到轮奸时至少是二、三个,多时有四、五个,人来人往整夜不断,乳房被日本兵乱抓乱捏得钻心的疼。日本兵不把我们当人看待,想怎么干就怎么干,用各种方法和动作对我们进行折磨,常常让人死去活来……
由于当时我年纪小,不来月经,来糟蹋我的日本兵从没有断过。
白天夜晚,我也都能听到其他姊妹们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和哭喊声,同时也听到日本兵的笑声。在藤桥慰安所的日子,我整天哭,要求他们放我回家。
后来,我的父亲通过在日伪砧板营当自警团长的亲戚陈仕连的担保,我才能够从藤桥慰安所被押回离家近些的砧板营日军军营。
我以为从藤桥慰安所回到砧板营日军军营,就可以经常与家人团聚,可是日本人就是不让我见家人的面,他们把我关在砧板营军营的一间房子里,春去冬来,衣裙破了需要添换,都只许通过看守人员递进来。日军砧板营军营离乌牙峒仅一里远,村里鸡啼狗叫牛哞声都能听到。
从不满15岁到18岁,我在日军慰安所里长达三年多,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,才能够逃出来与家人团聚。
回到村里后,人们就都叫我“日本老婆”、“日本妓”,人们歧视我,看不起我,仇恨我,我只好逃到吊罗山里躲起来,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。直到解放后,人民政府把我从山里请回来,分给我土地,给了我自由。
1957年12月,我30岁的时候嫁给了卓亚黑,卓亚黑是一个原国民党士兵,人又很丑,一直娶不到媳妇,所以就要了我,结婚一年后,卓亚黑就死了。3年后,解放军退役老兵卓开春与我结了婚。我和两位丈夫,前后怀过9个孩子,但是由于身体曾经受到日本兵长期的糟蹋,一直有病,前8个孩子有的死于腹中,或早产、流产。为了能够有一个孩子,我和丈夫到处寻医问药,经过多年治疗,1964才年生下了女儿卓梅英。
我的第二个丈夫在1996年病故。
由于有过那段经历,使我常常感到愧对女儿。女儿家的生活不富裕,为了不给女儿添负担,我一直一个人过。
广告、内容合作请点这里:寻求合作
咨询·服务